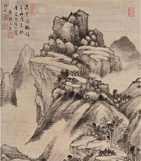|
·标题:历代雕版画的发展(上) ·作者:郭味蕖 ·发布人:管理员 ·日期:2010-10-24 历代雕版画的发展 (上)
我国伟大的劳动先民,在很早以前,便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这两大发明,对于全人类的文化发展,是有极大的贡献的。 在造纸术没有发明以前,没有雕版。最早的文字,有的刻在龟甲兽骨上(甲骨文),有的刻在青铜器上(商周钟鼎铭文),有的刻在玉和石上(石鼓文、诅楚文、石经)。到战国时候,又开始利用竹简和缣帛写字,但是竹简的分两太重,缣帛的价钱太贵,在文化的传播上和应用上,仍然是感到极大的不便。 据《汉书》上说,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时,宫中就有了用纸来包药的记载。后来汉尚方令蔡伦,在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时,又根据劳动先民的制纸经验,改用树皮、麻头、破布等造纸成功。造纸术发明以后,我们勇敢的先民,就又智慧地创造了印刷术。从此在书籍的产量方面,是空前地大规模地提高了。也从此具有民族风格、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雕版画,也开始萌芽和成长起来。 二十几年前,在新疆地方,曾发见了一张用雕版印刷的残破纸片。据说上面印着:“延昌三十四年甲寅??????家有恶狗,行人慎之??????”等两行文字。延昌是建都在吐鲁番的高昌年号,延昌三十四年,是公元五九四年,也就是隋朝的开皇十四年。这张残片,现藏英国。倘若这一考订正确,就足以证明我国在六世纪时,已经广泛地应用雕版印刷了。 唐宝历年间,有大唐宝钞纸币的发行。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有下诏不得私置日历板的记载。这些雕版印刷的遗迹,因了经过五代的变乱,幸而遗留到现在的,已是很少很少。公元一九00年,在王道士发见的藏在甘肃敦煌千佛洞中的两万多卷轴里,内中就有十分精致的用雕版刷印的金刚经和唐乾符四年(公元877年)、中和二年(公元882年)的历书等。这是我们劳动先民的手迹,也就是我国版画史上最珍贵的艺术遗产。 这些雕版印刷的版画,绘画的技术,非常精妙,雕版的手法,也相当纯熟。可见我国的雕版印刷,在唐五代时,就已经完成了一种风格,具有了划时代的辉煌成就。 雕版印刷术,很早就为教徒们用作传播佛教经典的工具。唐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曾带回了许多佛经。后来义净法师又从印度传来了捺印佛画的方法。在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上也曾有“拓摹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以砖裹之,即成佛塔”的记载。因了印度佛教文化的东渐,在雕版佛画的制作上,又显著地从原有的经验和传统中,溶化了印度的风格。近年在库车地方,曾经发见过有柄的佛模,可以和捺印一样地将佛像连续地印在纸上。有的卷子,只印佛像,一整卷有四百六十个之多。有的卷子上有鸟丝栏,在栏的上端,每行捺印佛像,像下书写佛名,这就是千佛名经。 根据敦煌千佛洞所发见的雕版佛画遗品来研究,其中金刚经扉画、大圣毗沙门天王图以及大随求陀罗尼轮、阿尼陀供养受持笺等,在绘画的构图上、雕版的线描和刀法上,已经树立了宋元明清插图本书籍的制作典范。 金刚经扉画――祗树给孤独园图,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刊印的。这是我国现存的雕版佛画纪年最早的一幅。幅长0.280米,高0.244米。图板的右上角,刊有“祗树给孤独园”的标题。经文后面,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题记。图中描写释迦牟尼佛正坐在祗树给孤独园的经筵上说法。长老须菩提正“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见金刚经)。佛的左右前后,站着两个勇猛的狮子,这是用来说明佛法的无边,也足以降服猛兽的。图的上部,有正在微风中飘动的幡幢。从瑞云中,正飞来了两个仙女。这幅版画的构图和人物的线描风格,和唐代的佛画相同,因着这幅是雕版的关系,线条更显得遒劲挺健而富有力量。因了刻工的技术精练,从长老须菩提面部的几条疏落的线纹,已能看得出,作者注意到了人物内心的表现,有意地在表达长老的虔诚严肃和苦修的性格感情。同时佛的面貌是那样的慈祥,贵人的面貌是那样的真实,作了显明的性格对比。为了显得画面的灿烂和完整,地面上更施以四方连续花纹的图案。通过这幅佛画就可知道,那时的雕版印刷技术,已渐渐由成长中逐渐地走向了纯熟和精练。 大圣毗沙门天王图,是大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雕印的一幅单独佛画。图版高0.394米,横0.255米。在敦煌壁画和绢画中,毗沙门天王像是常见的,但在雕版印刷中,是罕见的。毗沙门天王,是护法天神,是四大金刚中的北天门,能力很大,能管领天下一切杂类鬼神。据说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不空三藏作法,请毗沙门天王显圣,因此平定了外乱。所以唐时代就奉毗沙门天王为军神。图板的构图,是描写一个健壮的地神,从地下露出半个身子,用他的双手托住毗沙门天王的脚。毗沙门天王,右手执附旗的戟,左手托供奉释迦牟尼佛的塔。戴兜钵形宝冠,附有羽翼。两肩有火焰形射出,形成头光模样。眮部紧窄,长铠披肩,铠片作鳞状纹,衽裾有垂缘。在腰际横佩长剑。目光炯炯,胡须向上翘起,十足刻画了毗沙门天王的威猛性格。在天王的右面,是辩才天女,也称吉祥天,手捧花果。左面是一童子,童子的后方,站着一个体格魁伟的罗刹,面貌非常凶恶,正在用右手高举一个婴儿。这是因为佛经中载有毗沙门天王能变成小儿,普渡众生的记载。在天王的脚下,是沙丘配景,这说明了敦煌地带的特点。在图像下面刊有题记,从题记中,可以知道这一幅画是当时敦煌地方官吏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曹元忠请匠人雕造的。雕造的志愿,是希望“国泰民安,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的。曹元忠是继承张议潮以后镇守敦煌的长官。此外在敦煌发见了曹元忠雕造的与毗沙门天王同年月并刊有“匠人雷近美雕造”题名的观世音菩萨像及文殊菩萨供养受持笺等,都是雕版佛画早期的珍品。 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包括宋、金、元三个朝代。这是我国雕版印刷全面发展、百花齐放的伟大时代。这时中央、地方以及私人设立的书坊,因着一时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人民生活的向上和文化上的普遍提高,进一步发展了雕版印刷事业。这时雕版书籍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制作之精,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甚至某些地方,就是后来的明、清两朝,也不能相比。这时除了北宋首都汴梁外,浙江杭州(南宋首都)、福建建阳(产纸区)、四川眉山(文人区)形成了雕版印刷的三大中心。历侍十君的宰相冯道主持雕印的《九经》,和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雕印的五千多卷《大藏经》(即“开宝藏”),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吴越国王钱俶仿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基小塔故事,雕印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即“雷锋塔藏经”),都刊有精致的扉画或插图,这都是划时代的巨制。 在北宋时,雕版画的发展领域,已经相当广泛。当时刊印的经、史、子、集,以及小说、戏曲、医书、算书等等,都已大量地采用插图。例如《博古图》、《营造法式》、《素王纪事》、《针灸经》、《三朝训鉴》、《梅花喜神谱》各书,都是雕版印刷的典范。 南渡以后,都市行会工商业更加发展,一时旗亭、酒馆、瓦子、勾栏也普遍繁荣。同时盛行平话、讲史、戏曲等平民文化娱乐,所谓“开卷则市井能谙,入耳则妇竖咸晓”。为了供应人民大众的需要,一般平民文学插图本,便突飞猛进地发达起来。一时杭州众安桥一带书铺林立,有名的贾官人经书铺,便是开设在这里。 金代的雕版中心是平水(即今山西临汾)。平水的刻工,是北宋亡后从汴梁迁过去的。在十二世纪时,雕印了划时代的“金藏”,因为后来是藏在赵城广胜寺,所以又叫做“赵城藏”。里面的扉画,也十分精工。这是从公元一一四八年到一一七三年二十年间的巨制。这是一部国内外从来不曾著录过的孤本,在一九四二年八路军解放赵城时,才从日寇的魔爪里解救了出来,现在还有四千三百多卷。 当时平水书肆,也曾经大量出版了宫调唱本和单独的版画。十九世纪末叶,俄国旅行家柯基洛夫,在我国甘肃地方作学术探险时,曾在黑水城址(宋?西夏国)附近的古塔中,发见了一幅题着“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雕版印刷美人画。从画面上的题字,知道确系平水坊刻本。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富有装饰风的美人招贴画。从绘画构图的基础和雕版印刷的技术上看,比起金藏作手的能力,显然是高出许多,这是平水系雕版画中冠冕的作品。 这幅美人画,是描写历史上的四位美女,就是汉代的王昭君、班姬、赵飞燕和晋代的绿珠。从画面构图的富于变化而又生动活泼来看,可以知道在制作时,是费了一番缜密的布置功夫的。图中绿珠和赵飞燕立于前列,王昭君、班姬站在后面,绿珠面向左,余人面皆向右,这样便可能集中了视线,完成了画面上的多样统一。人身的比例,已经接近正确,颜面表情,虽然还不能显著地描写出个性,但使人看了,可感觉到是肃穆庄严,而又宁静寂寞。服饰衣冠的花纹,相当繁复,更显得雍容华贵。人物后面配有玉阶画栏、山石牡丹,也和宫廷贵嫔的身份,衬托得非常相称。在大字横书的标题下,刊有“平阳姬家雕印”的店标(平阳即平水)。美人的身边都有美人的题名。 元代时,杭州的刻书盛况也不亚于宋代。这时在杭州刊印的河西文(即西夏文)《大藏》,中瓦子张家书铺刻《唐三藏取经诗话》等平话小说、杂剧戏文。世传元刻本的《关大王单刀会》、《尉迟恭三夺槊》、《李太白贬夜郎》等,都书明“古杭才人”或“古杭书会”等刊记。福建建阳,这时也大量出版了新型类书,如《事林广记》、《宣和平话》、《三教搜神记》,图像也相当丰富。《事林广记》共四十二卷,十二册,元陈元靓撰,建安椿庄书院刻本。人物面貌衣着,典型蒙古人风格。刀法的浑沦古朴,是值得注意的。此外建安虞氏新刊的上图下文的至治本《三国志》,自“汉帝赏春”至“将星坠孔明营”,插图六十九幅。《全相武王伐纣平话》、《全相续前汉书平话》等,也都是刀马人物的绣像十分生动细致,奠定了一种插图本的典型风格。 |
|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