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好春光--郭怡孮画展》艺术研讨会(一)
·作者:
·发布人:管理员
·日期:2011-6-8
《大好春光--郭怡孮画展》艺术研讨会
时间:2011年6月8日上午
地点:中央文史研究馆
主持人:薛永年
出席研讨会的有:邵大箴、刘曦林、李树声、王镛、陈履生、张晓凌、李魁正、田黎明、梁江、唐勇力、郑工、安远远、尚辉、刘龙庭、李一、赵士英、杨悦浦、邵剑武、赵德润、贾德江、邵昌娣、郭怡孮以及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研究院的博士生、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共50余人。

薛永年:

现在的时光已经进入夏天,但是郭先生的展览给我们留住大好春光,对“大好春光”展览的定名和意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先生、国务院参事室王明明副主任对此都有很到位的评价。
今天研讨会让我来主持,实际是给我一个学习机会,认真听大家发言,积极向各位请教。郭先生是画花鸟画的中国画家,中国花鸟画历史悠久,一直在传承发展,传承借助创新,穿越了时空,创新也因为传承增加了厚度,毕竟每个时代的画家都有每个时代的任务,所以离开了时代的任务,传统就还在书本上,也没有办法实现传承。花鸟画是中国特有的画种,虽然不画人但是表现人的灵魂,历代出现很多名家、各种风格,改革开放以来有新的发展。
郭怡孮先生是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很强的艺术家,他一直在思考中国花鸟画怎么样应对当前的精神需要来表现新的视觉经验,中国花鸟画怎么走向现代。他不但是画家,更是美术教育家和美术活动家。在绘画创作上,郭先生是花鸟画领域的开拓者;在美术教学上他是国画教育的开风气者;在社会活动上他是新时期中国画坛的领导者之一。
郭先生有很强的创新意识,但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中国画,他的父亲是我们敬仰的郭味蕖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郭味蕖先生就发扬革新精神,有效地整合了传统,刷新了小写意花鸟画的精神体貌,当时就获得广泛的好评。郭怡孮先生继承家学,又在艺术学院受到了系统的训练,文革前已经初露头角,文革后进入了设在藻鉴堂的中国画创作组,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接着就受聘到中央美院执教。郭先生拥抱自然,整合传统,讴歌生命的光辉,表现春光的灿烂,体现大自然的律动和节奏,反映时代的审美趣向。他的艺术极大地拉开与传统的距离,不再是黄家的富贵,也不是文人的野逸,更不是一般的庙堂气、山林气、书卷气,是启功先生所称道的“大麓画风”。这个说法是启功先生在一首题诗里体现出来的:“喜看丹碧出深丛,黼扆宏开大麓风。太液波光无限好,上林春色十分红。”他的诗点出了郭怡孮花鸟画的几个特点:色彩鲜艳、富丽堂皇、构图大气、层次丰富,其中还点出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既有庙堂气还有山野的生机,把山野的生机引进了“上林”、“太液”的殿堂,概括得非常准确。郭怡孮“大麓画风”的作品追求大画幅,大气势,大花朵,大内涵,大的生命律动,超越小我的社会文化内涵。他更以色彩的抒情性与图式的象征性,深化了作品的立意,比如:讴歌香港回归的《日照香江》,呼唤尊重自然的《我的内罗毕宣言》。
近年来他的作品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加强了笔墨的抒写性,包括没骨画法的书写性,色墨的流动性,调动的和谐感,还有一种突出了色彩的辉煌夺目,使用了金银箔,也增加了笔触的写意性和色彩的丰富性。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画的发展被理论家概括成两种路数:一种是借古开今,一种是融合中西。其实画家并不这么绝对,郭味蕖先生的花鸟画整体属于借古开今的小写意,局部也不乏融合中西的地方,甚至细部吸收了写实因素,但是用得非常好。郭怡孮先生的艺术更接近融合中西,甚至比他父亲更多吸纳了西画的成分,一个是强化了色彩,一个是注重构成,他使用的色彩更多,更不是假定性的随类赋彩的色彩,而是有现场感的,直观动人的色彩感觉,雅俗共赏。他的画非常抓人。郭怡孮先生的作品很少再画传统的折枝、盆供、丛艳,也不再以笔墨为艺术中心,但是放大的花头,成片的花海,饱满的构图,瑰丽的色彩,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色墨关系与平面的虚实关系。他实际上是力求传统学养和现代审美结合起来,寻根意识和全球意识结合起来,探索一种便于中西沟通的具有普世性的绘画语言。对于郭先生的探索与突破尽管也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看法,但都会看到他扩大了花鸟画的精神内涵,强化了花鸟画的视觉冲击力。如果说郭怡孮先生的父亲郭味蕖是老一辈名副其实的学者型画家,郭怡孮先生不仅同样是按学者型画家来塑造自己,同时,是画家中富于思想的理论家。在85新潮掀起之后,一时间出现了中国画的危机论,当时反对危机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潘公凯,他发表了“倡导和谐文化的绿色绘画论”,郭怡孮先生敏锐发现了潘公凯这种主张的价值,专门把潘公凯请到中央美术学院作系统的讲学,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
多年来郭先生出了不少颇有影响的理论命题,像大花鸟意识、像技法重组、像创立新程式、像重彩写意、像三个灰箱即工笔与写意、泼墨与重彩、山水与花鸟两极之间来探索那种丰富与和谐。所以郭先生的理论和实践充满了问题意识,他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了花鸟画的精神内涵和现代功能,艺术的个性与时代的共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中与西,传统与现代,色墨与色彩,写生与写意,生态与城市,艺术家学与学校教育,艺术与生活等等。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研讨郭怡孮先生的艺术,回顾他的经验已经远远超过了给他个人艺术做历史定位的问题,而是怎么来认识中国花鸟画的继承和发展,固本自强与包容开放,怎么繁荣发展中国画的问题,怎么去寻找中国传统的生长点,怎么使花鸟画走向世界为人类做贡献,来保护环境,来适应今天的需要。
下面请郭先生讲几句。
郭怡孮:

今天请这么多专家来参加研讨会,首先表示非常的感谢。今天在文史馆来开这个会,感谢中央文史馆提供这样的机会,文史馆是研究学术的最高学府,所以选择这儿我也有这个意思,离开展览会现场的光彩,在展览会现场人们初次看到我的五颜六色的画会有一种比较激动的心情,对于学术我们应该离开那样的场地,回到一个非常平静非常深沉的研究学术的氛围。
这几天我听了一些好评,大家对这个画展感觉很喜庆,很有朝气,一些群众表示祝贺,那是一个表面现象,还有很多深层问题,我自己非常忐忑,我是一个画家,我只是提供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一种实践的路子,我也有过许多思考和实践,包括大花鸟意识,包括技法重组、重彩写意、写交响曲等等很多方面,其实在理论上都是不成熟的。
今天在大家面前,在理论上都有深沉思考的各位理论家面前,希望大家帮我思考,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花鸟画、中国画怎么发展,给我提一些比较具体的,不仅只是赞扬的话,这是我心里想的。因为我自己提出的一些东西,我自己解答不清楚,在这些问题上构不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只是我自己的探索,自己的实践,最多是提供了实践的一个方面,特别是我有很多学生,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了,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怎么把我的学术做踏实,希望真正踏踏实实的做点学问,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的方向。
有人说这次画展特别好,特别令人激动:“重塑了中国花鸟画的尊严”;也有人说:“这是当前政治宣传画的花鸟版”。这些问题是很尖锐的一些问题,到底画家在当前社会应该怎么样做,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展览会,对我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具体的改进的想法,对中国的花鸟画的发展到底应该怎么样走,怎么走多元的,走更宽阔的道路,给社会提供一些思考,谢谢大家。
主持人:
收到两个书面发言,一位是国务院参事室的郭瑞先生,还一位文学家雒青之。
李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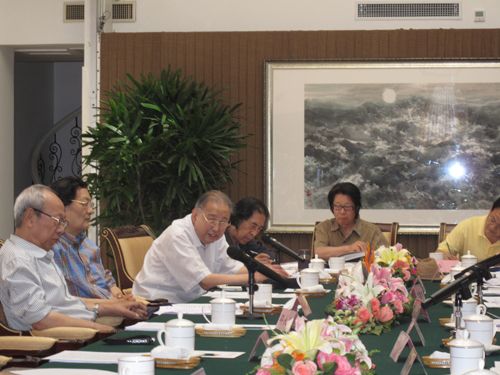
郭怡孮这次展览是他近50年的劳动,集中展示他50年来所完成的这么多的作业,这么多成绩,这些成绩大家到美术馆一进门都会感到,一进展览厅就感觉春光明媚,繁花似锦,确实是呈现了大好春光的效果。他想要给大家表现的东西彻底让人感觉到,让每个欣赏者可以欣赏到美感,这个很不容易,有时候心里想做,但出不来效果。
这些年他在花鸟画另走一条路,这条路也算是闯出来了。这次展览和他以前的展览相对照,比过去确实更加成熟。为什么?表现在几点:
一个是他一开始往那走的时候,让人觉得他主要搞装饰,装饰性很强,但是觉得缺了点什么,当时起个外号,叫花被面。这次展览和那个时候相比明显的不同,章法上不像以前,花卉画活了,画的非常自然。艺术回到自然的效果是很高的境界。不像以前就是在画花,让人感觉只是一朵朵的画,现在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活的花卉绽放。
色彩比过去更艳。但是艳而不俗,这个很难做到。有时候求艳觉得太适应大众需要,有点往俗走,但他的艺术效果绝没有那种,还是很雅的,画活了,很雅,而且颜色这么有冲击力,那个效果出来了,他已经达到了高度。他已不同于原来北京的花鸟画,比如田世光先生他们画的花鸟画的路。和他的父辈相比,除了竹子还有老郭先生的影响,其他方面他比郭味蕖先生要放开的多,更加体现一种心情,有时代精神。为什么?因为这些年确实每个人感觉到大家心情舒畅,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特别是经历种种政治运动的人大家都会有所感觉,改革开放初期,廖冰兄画的漫画,罐子虽然打开了,但胳膊腿伸不开。经过30年所有知识分子胳膊腿伸开了,那种境界在他的画里体现出来了,这个不能说是宣传画,是非常真实的情感表达。大家都感觉到的,普遍的知识分子,大家的地位和生活中的实际感受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内心发出来的对今天时代的歌颂,这是一种心情的表达。我很钦佩他在身体这么不好,又做了支架,又是血糖非常高,真是玩命玩出来的成绩,应该说已经是走向了成熟,这次展览确实给人完全的新面貌,连我的老伴都说郭怡孮真进步了。她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大家恐怕一般观众也会同样感觉到。
杨悦浦:

我和郭怡孮先生是同班同学,年级比他大两岁。我们那个学校是个师范学校,后来改成了北京艺术学院,但是主要培养老师,我们学校按照中学基础教育这样的范围来教学,好处是学生眼光开,不好的是很容易被一些模式固定住。在学校的时候我就觉得郭怡孮画画有一些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也可能有他家里的教育,主要是他自己的思想比较活,他那时候知道到徐悲鸿纪念馆看画,我们不敢想。从画风和想法就不一样。
我对他这么长时间观察,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好像一说到思想我们好像都认为是毛泽东思想或者是伟人思想,其实我觉得一个画家没有思想根本就画不成画。他的思想也就是最主要的东西必须要融进他的生命历程之中。他每时段有自己的思想提出来,到底思想的社会意义怎么样大,在努力实践,他是自己要做,不管提出大花鸟精神也好,他提出自己的很多建议也好,他在努力实践。
1993年全国国画展,他拿出一批作品变化很大,这种画风是他去了法国之后,把他原来从西双版纳纯写生的角度走进他主观的意识里了,他的画马上有新的面貌。他如果没有这种的想法,没有这种思想的变化,把自己的东西变化出来,他的作品不可能出现变化。
当然这个思想要实践,实践完之后自己要有一个检验的过程。他也很认真,每到一个阶段办一个小画展,我看他主要是为了总结自己,他出版一些东西,不是为了给别人看,他是总结自己走的路,在郭怡孮身上表现的非常明确。比如说我们看他从1993年的风格变化到现在色彩这么强烈,郭怡孮这样面貌的中国画,是开拓一个新的视觉领域,如果没有特殊的想法肯定是做不成的。今年郭怡孮71岁了,我们看他70年变化,从艺50多年变化,其实是一个思想的变化,他的成功就成功在这里。
|